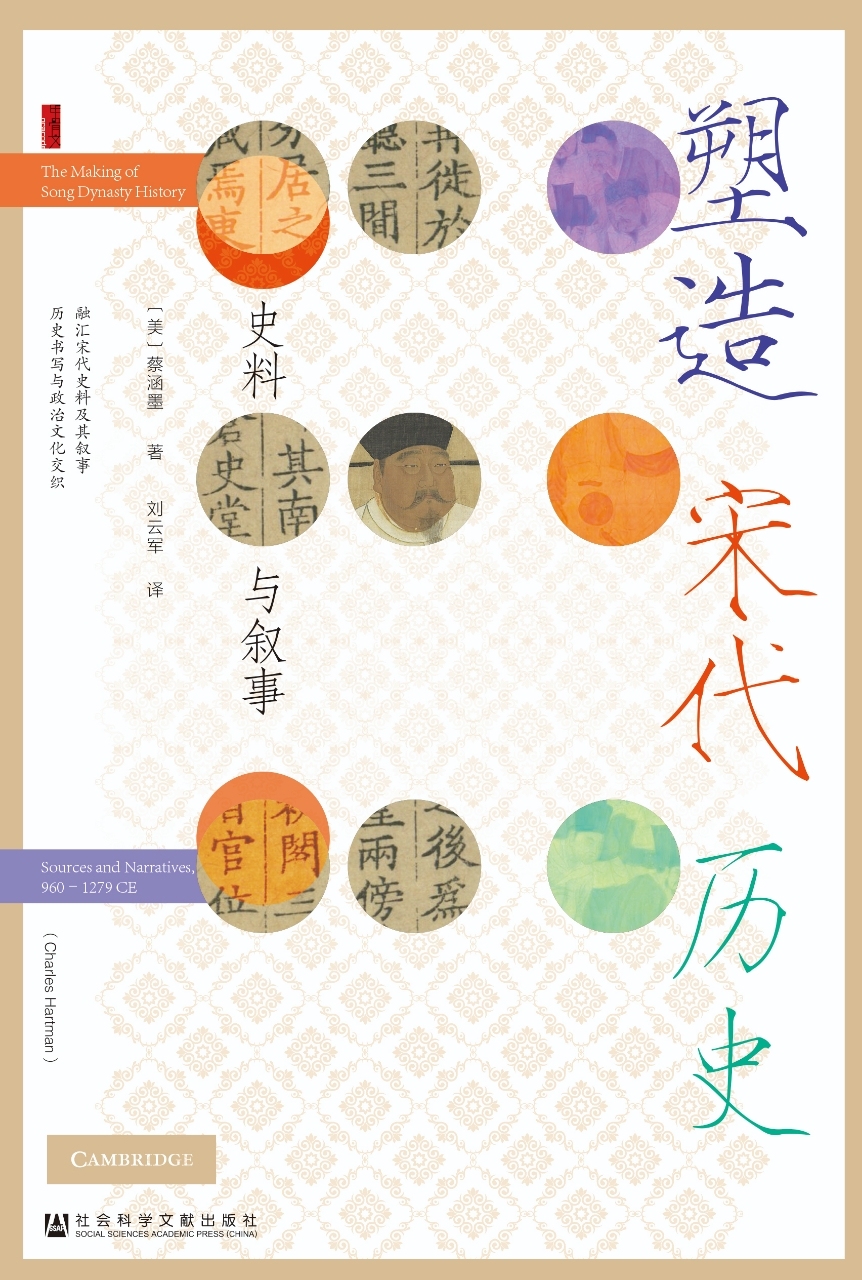
《塑造宋代历史:史料与叙事》,[美]蔡涵墨著,刘云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12月出版,644页,11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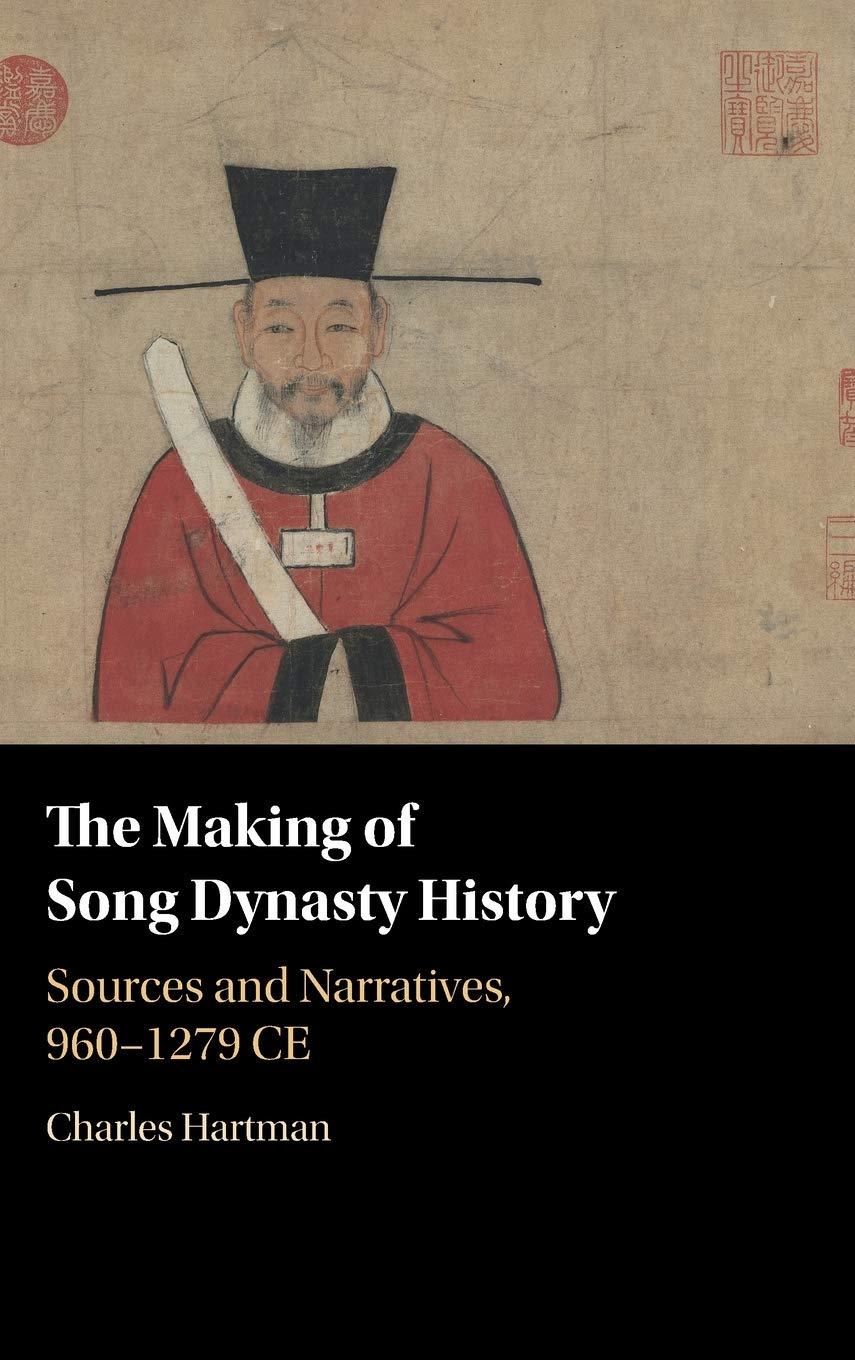
The Making of Song Dynasty History: Sources and Narratives, Charles Hartm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400pp.
蔡涵墨(Charles Hartman)教授近年出版的著作《塑造宋代历史:史料与叙事》是我认为当前宋史研究中极具开创性的成果。该书不仅在理论上提出了深具解释力的分析模型,也在方法上推动了我们对史料本身性质与作用的重新思考。作为一名从事宋代政治与宗教史研究的学者,我感受到这本书在切实地改变我们所处的学术生态。
正因如此,我对庄语乐先生日前撰写的书评《宋代历史是被“塑造”出来的吗?》颇感遗憾。他的评论主要集中在一些论证细节的问题上,继而对蔡著中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倾向提出严厉批评,却未能准确呈现本书最重要的论点:蔡涵墨试图使读者理解,宋代史料并非绝对中立的事实记录,而是不同政治力量在各自历史书写的话语体系和制度框架中长期博弈、不断塑造和传承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一种儒家制度主义(Confucian institutionalism)的叙事最终胜出,从而造成了我们现今流行的对宋代政治史的理解。如果忽略了这一核心问题,那便等于错过了本书对当代宋史研究最根本的挑战与启发。
我之所以决定撰写这篇回应性的书评,也有着个人的缘由。在我过去的学术成长过程中,曾对“谁在书写宋代历史”这个问题产生过长期的困惑。我相信个体的学术经验,往往能帮助我们更具体地理解一部作品的意义。因此,这篇书评不只是一次专业性的评论,也是一次带有反思性质的写作。我希望通过回顾自身的学术轨迹,解释蔡涵墨这本书为何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性,并展示它如何为我们开启理解宋代历史的新路径。
为了尽可能忠实于原著的论点与用词,在本文中,我引用《塑造宋代历史》时将依据英文原版的页码。读者若手头持有中文版,也可通过章节内容在译本中找到相应段落。这种处理并非出于对译本的不信任,而是基于一种基本判断:翻译本身就是一个重新建构与再诠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语义与语气或多或少都会有所流失,尤其是像蔡涵墨这样的著作,其许多理论关键词在语言迁移中往往承载着不同文化语境中的歧义或张力。我将在后文进一步说明这种中文读者阅读译作的复杂性。最后,我也希望借这次书评的机会,进一步思考《塑造宋代历史》对整个宋史研究领域可能带来的意义,并简要介绍蔡涵墨近年来出版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宋代中国的政治结构》(Structures of Governance in Song Dynasty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这本书尚未有中文版问世,但可以看作是对《塑造宋代历史》的延伸与深化,标志着蔡涵墨不只是对既有历史叙事提出批判,更在尝试重新构建我们理解宋代政治与社会运行方式的基本框架。
蔡著在处理什么样的问题:从我个人的学术经历说起
在2010年代的前几年,我在北京读研究生,主修宋史。当时我一直被一个问题困扰,而这个困扰其实来自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宋代政治史的路径。一方面,那几年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非常热门,在研究宋代的年轻学生中几乎是人手一本。这本书强调儒家士大夫在宋代政治中的地位,认为他们在君主面前有时可以分庭抗礼,甚至能够公开抗议皇权的决定。这种观点塑造了一种“士人政治”的理想图景,宋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说法也因此广为流传。
但与此同时,我也发现自己的老师中有学者对此深表怀疑。比如资深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就对余英时的论点不满。他倾向于更接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解释路径,主张宋代士大夫并不值得美化,是腐朽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更进一步地,他甚至觉得,一些宋代历史的译作用“精英”(elite)这个词来形容这些士大夫本身就是不恰当的,因为“精英”应当意味着某种道德高度,而这些人并不配得上这样的道德称号。
这样两种观点,在当时的我看来各有体系、各有根据,却又几乎无法调和。一种视宋代为儒家士大夫能够与皇权分庭抗礼、共同执政的黄金时代;另一种则视儒家士大夫为自我包装的利益集团,道德上早已败坏,行为上多出于功利计算,远谈不上什么“为天下苍生”的理想主义。更重要的是,这两种说法都能找到自己的史料依据。我当时常常感到困惑:如果宋代历史能被如此不同地讲述,那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这段历史?
蔡著的主要论点
蔡涵墨《塑造宋代历史》所提出的问题,与我在研究生时期所遇到的学术困惑高度相关。这本书并不试图解决宋代的政治生态是否可以被定义为具有高尚理想的“士人政治”,而是关注另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今天所依赖的宋代历史叙述,是如何被书写出来的?是哪些人,在何种体制、语境与政治逻辑下,决定了哪些材料被保留,如何被解释,又为何以那样的方式被传承?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所提供的并非是宋代政治史的重构,而是一种理解“历史为何如此”的路径。只有了解宋代历史书写的形成,我们才能更有把握地重构这一时代的历史。
概而言之,这本书挑战了一种深植于宋代以来的史学传统,即以儒家立场为核心的历史解释模式。蔡涵墨指出,这种解释体系不仅主导了宋人自身对历史的编写方式,也深刻影响了后世对宋代的理解。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聚焦于五类关键史料的成书背景与传世过程:包括《宋会要》、《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道学史家编纂的历史,以及元代修撰的《宋史》。蔡涵墨不仅分析这些史料的内容,更深入挖掘它们产生的政治与知识语境,进而揭示出编史者试图传达的意图与信息。
下半部分则讨论这些史料如何共同构建出一套“宏寓”(grand allegory)式的历史叙事。所谓“宏寓”,是一种长期主导对宋代理解的大叙事框架,它产生于两种政治理念之间持续的张力之中:一是五代时期以技术官僚(technocrats)为主导,强调对君主个人效忠的体制运作方式;另一种则是在庆历年间逐渐形成的儒家制度主义(Confucian institutionalism),主张通过道德教化与制度建构来限制君权。蔡涵墨指出,宋代儒家史家往往倾向于后者,并通过重新组织历史材料、建构一套理想化的王朝往事,来对当下政治加以批评或引导。这种史学写作不只是记录,更是一种具有规范意图的建构(pp. 1-22)。
在这里,我需要稍作说明。蔡涵墨在书中提出的technocracy一词,若直接译为“技术官统治”或“技术官僚体制”,在中文语境中可能引发一定误解。在宋代官制中存在所谓“伎术官”,指的是那些掌握特定技艺、直接服务于皇帝的技术性职位,例如医术、天文、音乐等。这类官员虽被称作“伎术官”,但与蔡涵墨所指的technocrats并不相同。在英文语境下,technocracy指的是一种统治的方式。在这一方式下,那些在特定领域拥有专业知识与技能的人会因其专业能力而获得可观的政治权力。蔡涵墨认为这类技术官僚构成了五代时期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往往是临时被任命的专员,因其在财政、军事、调度等领域的突出能力而受到重用。他们未必出身望族,也未必通过科举系统,但却拥有在体制中实际运作的权力。因此,尽管“技术官僚”这一中文翻译或许还有待进一步斟酌,但为了行文的便利,我仍保留这一用法。理解这一术语的准确含义,对于把握蔡涵墨所描述的五代宋初政治生态,以及他后续提出的“宏寓”结构,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蔡涵墨的分析中,宋代历史书写并非单纯地出自儒家史家的道德判断或对皇权的歌颂,而是在儒家士大夫与技术官僚这两种政治逻辑之间的长期张力中,被有意识地组织与诠释出来的叙事结构。然而,正是这一层理论的复杂性,在庄语乐的书评中被显著地简化甚至误读。他将“宏寓”理解为一个对皇室的单向赞颂系统,忽略了其本质上由儒家士大夫主导、意在规训皇权的建构性过程。在庄语乐的书评中,有一段话颇具代表性地反映了他对蔡涵墨观点的理解偏差:
这部分在“史料”之上,进一步将一切宋史史料视作一种“塑造”,历史编纂作为政治“工具”,“除了谄媚皇室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力量推动实录中叙事的形成”(导论,第22页),也即,宋史史料对作者而言主要是“宏寓”,“宏寓”又是由“谄媚皇室”和“共治工具”两大要素组成的。(引文中出现的页码为中译本页码)
这段话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概括了蔡涵墨对史料建构性的强调,但问题在于,庄语乐把一个本质上复杂而富有层次的理论,简化成了一个单一方向的政治工具论:仿佛历史书写的全部动力都是“为了谄媚皇室”。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实录本身确实是皇权体制下的产物,它的编纂目的主要是为了记录皇帝的日常与功绩,从结构上服务于帝王形象的建构。特别是实录的编纂在宋代需要通过皇帝的审查,而这一过程被称作“进御”(p. 8)。从这个意义上说,蔡涵墨使用adulation(中文译为“谄媚”)一词并非没有依据。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英文中的adulation含有“过度称颂”之意,其语气虽批判但不带中文“谄媚”一词那种强烈的道德贬义。若读者仅依据中文译词来理解原书,很可能会误解作者在语言上的语气与立场,进而误判他的整个论点。
其次,庄语乐将“历史编纂作为政治工具”理解为一种对皇权的服务机制,这种看法虽然不完全错误,但却遮蔽了蔡涵墨“宏寓”概念中的另一个支柱。蔡涵墨提出,“宏寓”不仅由“对皇室的赞颂”构成,更重要的另一部分是其儒家制度主义的功能:即儒家士大夫通过史料的选择、叙述与解释,来向当时的皇帝施加规训与批评。这种历史建构不只是为权力服务,它本身也是与权力博弈的一部分。
更关键的一点是,庄语乐似乎将“宏寓”理解为一半来自技术官僚对皇权的赞颂,另一半来自儒家士大夫对皇帝的规劝之言。然而,蔡涵墨的分析并非如此对半切割,而是明确指出,“宏寓”本身就是由儒家士大夫主导发起的:他们选择、整合、组织史料,构建一个具备政治教育目的的历史叙事结构(p. 19)。即使是那些看似赞美皇室的记录,也可能被置于反面教材的语境中,用以提醒当朝皇帝什么是糟糕的治国方式。若忽视这一问题,就会误将“宏寓”看作是皇帝与士大夫之间的分工合作,而不是士大夫以史笔为武器进行政治介入的一种体现。
正因如此,庄语乐虽然引用了蔡涵墨关于“谄媚”与“共治”的双重结构,但他既未处理清楚“宏寓”的主导者是谁,也未充分展现这一概念中所包含的政治批评张力。这种简化的解释方式,不仅削弱了蔡涵墨原本理论中的复杂性,也容易让读者误以为《塑造宋代历史》只是在做一种负面的批判宋代史学的工作,而忽略了它所揭示的那种士大夫借助史料塑造话语、争取政治权力的活跃姿态。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译作:一个具体的例子
在这部分,我想通过庄语乐书评中对《太平故事》的讨论,来回应庄文中对《塑造宋代历史》的某些批评。这是一个比较细节性的讨论,涉及英文本的翻译、中文史料的理解,以及作为书评者对原书论点的把握能力。之所以选择展开这个案例,是因为它能清楚地说明一个更大的问题。庄语乐在书评中提出蔡涵墨的著作存在“硬伤”,但他所列举的证据其实只是全书中极为有限的一小部分,既不能代表整本书的论证水平,也不足以支持他对全书的否定性评价。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案例中,我们会看到,庄语乐对史料的使用和理解并不足以支持他想要得出的结论。换句话说,他试图通过一些看似具体的考证来证明蔡涵墨的研究“站不住脚”,但庄文的指责却经不起推敲。也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这个案例值得被认真地拆解与分析。
在讨论《太平故事》与《国朝会要》的关系时,庄语乐首先质疑蔡涵墨所谓“《太平故事》是《国朝会要》节本”的说法,认为作者把两者的关联分散在不同章节,却始终缺乏确凿证据来证明这种从属关系。他尤其指出,蔡涵墨将《太平故事》和《国朝会要》的进呈归于王洙。然而根据庄语乐的理解,这部书应由富弼领修并上呈,王洙虽在史院任职,参与编纂,却并无明确证据表明由他进呈。然而,这样的批评其实是建立在对英文原文语义的误读之上。
蔡涵墨写道:Wang Zhu submitted the first huiyao…; the Precedents…followed five months later.(p. 28)也就是说,他只明确了王洙进呈《国朝会要》,而《太平故事》的出现是在时间上“随后”,并没有说“由王洙进呈”。事实上,他在下文明确指出,是富弼命令将《太平故事》分发给中书门下与枢密院的官员,供政策参考之用。因此,蔡涵墨并没有逻辑上将《太平故事》归为王洙所进,而是庄语乐根据中文译文中不够严谨的表述作出的判断。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庄语乐认为蔡涵墨提出《太平故事》是《国朝会要》的节本。然而,若我们回到英文原文,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蔡涵墨的表述是:The Precedents… was a more focused subset of the former.(p. 28)这一句中,“subset”意指“子集”,是一种在内容主题上更聚焦的关系,并不等同于“节本”或“节选”关系。译者将这一词译为“节本”,实则是一种过度阐释。这一翻译误导了庄语乐,使他以为蔡涵墨在主张《太平故事》是从《会要》直接节录而来,进而批评其“无证据”。但如果读者参照英文原文,就会发现这种批评其实基于翻译的误解,而非对作者原意的准确把握。
当然,我无意苛责译者。翻译本身就是一件极为艰难的工作,任何一个认真从事翻译的人都会承认:在不同语言之间传递复杂学术概念时,语义的偏差、语气的误读,乃至措辞的选择,往往都难以做到尽善尽美。我们固然应当努力追求精准、严谨的表达,但与此同时,也需要给予译者更大的理解和宽容。因为在翻译的过程中,语义的流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能因为某些措辞处理的偏差,就否定一部著作的全部价值。
正因如此,面对像《塑造宋代历史》这样具有理论野心与结构创见的著作,我们更应将注意力放在它试图提出的核心问题和整体框架上。蔡涵墨的真正贡献,不在于他是否在每一段文字中都万无一失地还原了某一条史料,而在于他是否拓展了我们对宋代历史的理解方式,是否提出了打破旧有史观的新思路,是否帮助我们从既有叙事中脱身出来,重新看见被遮蔽的结构与逻辑。这些才是学术讨论中更值得关注与争论的地方。若只在个别术语或细节上反复咬文嚼字,不仅可能误伤译者,更有可能错过一本著作真正想带来的视角转换与理论突破。
庄语乐接着从文本形态与内容入手,试图进一步否认《太平故事》与《国朝会要》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他援引《太平宝训政事纪年》对《太平故事》的大篇引文,强调其与《会要》在呈现形式和文本上并无重合,因此认定《太平故事》不可能是《会要》的节本;他又特别提到书中“臣弼等释曰”的评语体例,认为如果作者真正研究过《太平故事》,就会发现它更接近石介的《三朝圣政录》,而非《国朝会要》。但如前所述,蔡涵墨原文使用的是“a more focused subset”,即“一个更聚焦的子集”,而非“节本”这一在中文语境中带有“内容节录”含义的术语。这一翻译偏差本身就已经偏离了蔡涵墨的原意,因此庄语乐建立在“节本”之上的这套批评,其实并未击中原作者的论点。
更值得注意的是,庄语乐所强调的“臣弼等释曰”这一表述,其实反而有助于佐证蔡涵墨的观点。《太平故事》的编纂,确实是富弼主导下一个集体协作的产物,而非孤立于其他官修项目之外的独立创作。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三记载,宋仁宗确曾诏命王洙、余静、孙甫、欧阳修等人共同编纂“故事”。仁宗的决定是由于富弼所上的奏章,富弼也因此成为编纂的主导。在同一时期,王洙正在负责《国朝会要》的编修工作(《长编》卷一〇九、一四八)。这些明确的编修背景说明,《国朝会要》与《太平故事》不仅在时间上紧密相连,在人事安排上也有重要重叠。蔡涵墨提出两书可能共享部分编修素材,进而将《太平故事》视为一种面向皇帝、具有政策教化意图的“更聚焦”的文本,这是一个完全合理且有史料支撑的推断。
庄语乐继而质疑蔡涵墨对富弼政治意图的解读。蔡涵墨在书中认为富弼的《太平故事》强调了“儒家‘仁’的美德是宋初治国的基本性质”。但在庄语乐看来,这其实是对史料的误读误用,因为富弼仅仅在称颂宋太祖平定四方的过程,并未上升到所谓“治国性质”的层面。然而,若我们细读原文,会发现他的理解其实过于简化了文本的内在逻辑。富弼在《宋史全文》卷二中的原话如下:
富弼曰:太祖之爱民深矣。王师平一方而不为喜,盖念民无定主,当乱世则为强者所胁。及中国之盛,反以兵取之,致有横遭锋刃者,遂至于感泣也。推是仁心而临天下,宜乎致太平之速。
富弼在叙述宋太祖平定天下的过程中说到,太祖对百姓的爱护非常深厚。当王师攻下一地,他并不因此感到喜悦,因为他担心百姓在失去稳定君主的动荡时期,会被强权所胁迫;等到中原强盛后,中原统治者又兴兵征伐,致使一些百姓平白遭受战乱之苦。富弼认为以这样的仁心来治理天下,也就难怪能如此迅速地实现太平。这里所强调的“仁心”,其实正是富弼在借由太祖的经历提炼出一种可供当政者借鉴的政治理念。所谓“致太平之速”,并非简单指战事进展迅捷,而在于太祖目睹百姓疾苦后生出深切同情,并以此仁心治理天下,才最终迅速安定四方。
蔡涵墨正是敏锐地捕捉到这种由历史经验通向政治理想的转化,将其纳入“宏寓”阐释之中。因此,他指出《太平故事》强调“仁”作为宋初治国理念,并非曲解史料,而是对富弼话语深层政治意涵的恰当把握。相较之下,庄语乐将“仁”的表述理解为纯粹的历史叙事,而非政治寓言,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是对文本厚度的简化。
在进一步探讨《太平故事》的政治意义时,庄语乐对蔡涵墨提出了更为尖锐的质疑。他认为蔡涵墨误读了罗从彦《遵尧录》卷四的一段文字,误认其把仁宗统治时期的成功归因于《太平故事》所确定的政策。庄语乐认为罗从严仅仅是在阐述富弼的撰述意图,因此蔡涵墨所谓《太平故事》“成为界定祖宗成就的史学基础”,在他看来只是牵强的推断。然而,若我们仔细阅读罗从彦的原文及其语境,会发现庄文这段批评本身存在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罗从彦的原文如下:
臣从彦释曰:仁宗承平之久,纪纲不振,盖因循积习之弊耳。然能为太平天子四十二年,民到于今称之,以德意存焉故也。况德意既孚于民,而纪纲又明,则其遗后代宜如何耶?此弼之所以奋然欲追祖宗,思刬革也。
罗从彦在解释富弼编修《太平故事》的用意时认为,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虽能长期保持太平,但其实朝廷的法度已经渐渐松弛。他之所以还能做个太平天子,关键在于其推行德政的意图深植人心。正因为仁宗的“德意”已深得民心。罗从彦才设想,如果再辅以严明的法度,那留给后代的典范将会多么可观!在罗从彦看来,富弼编纂《太平故事》正是为了搜集祖宗成法,来弥补仁宗在“纪纲”方面的不足。从语气来看,罗从彦此处对富弼编修《太平故事》褒奖有加。
可见,这段文字的重点并不在于赞美仁宗治下的太平已臻完善,而是通过一种温和却清晰的批评,指出仁宗虽以德得民,治理仍有不足,特别是在纪纲方面。富弼因而希望通过编辑《太平故事》,收录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的政治先例,用以规谏仁宗,使其既能承续德意、又能重振法度,实现道德教化与纪纲的双重完善。
庄语乐将这段话简单归结为“富弼的撰述意图”,既没有说明清楚撰述的目的为何,也模糊了罗从彦本人的政治判断和修史动机。至于蔡涵墨的解读,他确实将这段话简化为将仁宗朝的成功“归因于《太平故事》确定的政策”,略有误读。但若从更大的结构来看,他的基本判断仍然站得住脚,甚至可以说罗从彦的这段话进一步强化了蔡涵墨的论点:《太平故事》确实在当时被一部分士大夫视为一部具有政策启发功能的“祖宗成法集”,其史学功能与政治功能之间的界限是模糊而紧密交织的。
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庄语乐的书评其实并未完全掌握蔡涵墨原著的本意。其批评的出发点,有一部分建立在译文的层次之上,而对英文原文的语义把握并不总是准确;同时,他对史料本身的解读,也存在明显的选择性与片面性。这些因素叠加起来,使他对蔡涵墨的某些严厉批评显得力道过重,论证也略显仓促。
我无意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真正重要的是,我希望通过这一例子指出在阅读、翻译与评论之间,其实横亘着非常复杂的理解链条。当我们面对一本英文著作,尤其是那些试图以理论与方法重新架构史学视角的作品时,译者与读者所面对的挑战远比表面看起来大得多。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诠释,而任何诠释都可能带来意义上的偏移。当我们试图用中文去阅读一部英文作品时,事实上已经处于一种“再建构”的过程中。也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我们更应以一种温和而同情的眼光去看待这些通过翻译引进的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而不是急于用“硬伤”或“错误”去否定一部作品的整体贡献。否则,我们可能真正错过的是这些作品给予我们的新视角、新问题意识。这不仅关乎我们如何理解中国历史,更关系到我们如何以开放的姿态参与世界范围内的史学对话。
一条重新理解的路径
如果说《塑造宋代历史》的核心工作在于拆解一套由儒家史家建构的“宏寓”,那么蔡涵墨的续作《宋代中国的政治结构》(中译本尚未面世)则试图在这个基础上,重新建构一套理解宋代政治运作结构的分析框架。这部续作提出了一个新的模型来解释宋代的国家权力结构:“技术官僚与儒家制度主义的连续统一体”(technocratic–Confucian continuu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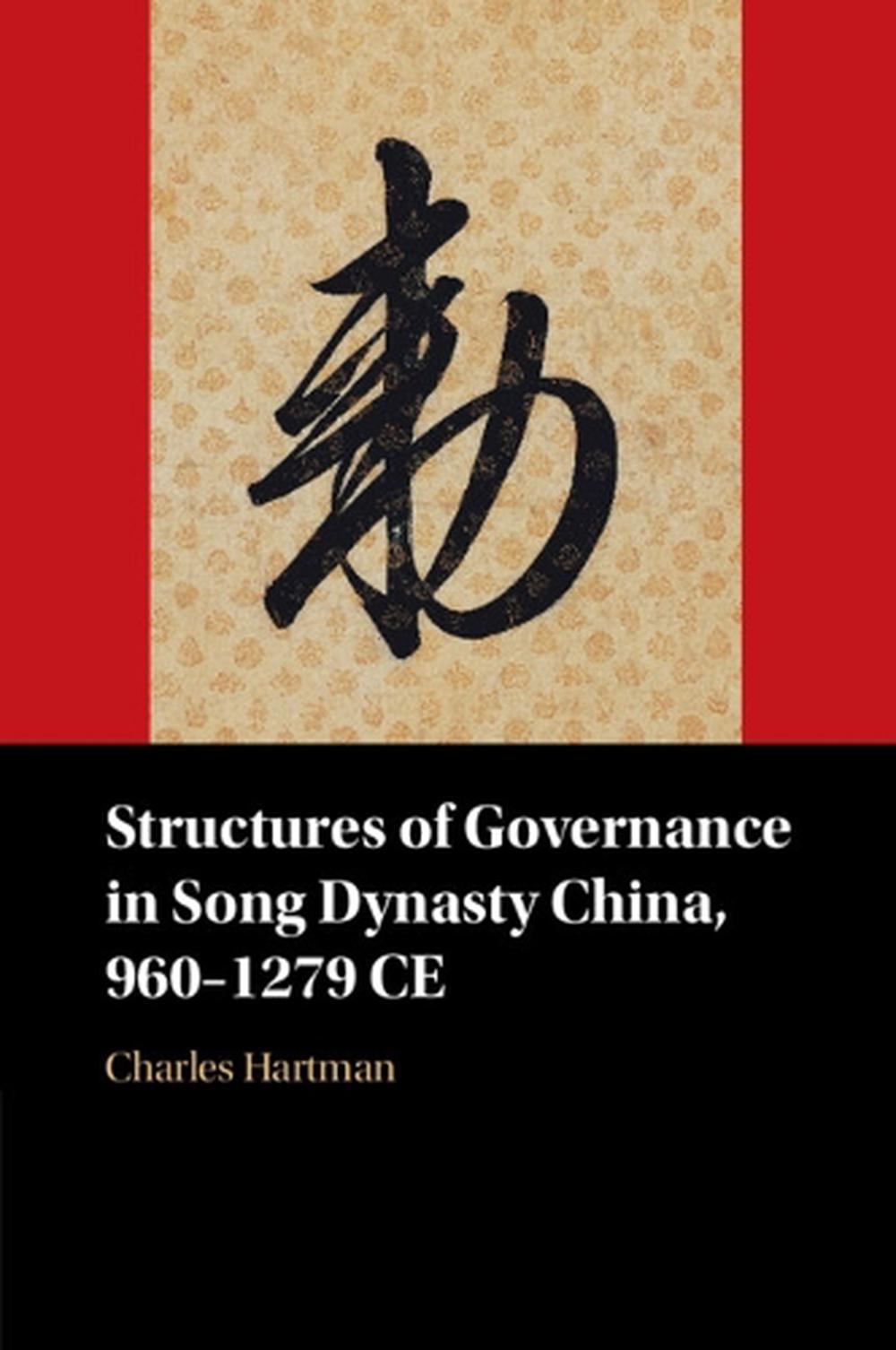
蔡涵墨著《宋代中国的政治结构》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连续统一体”(continuum)并不是历史事实本身,而是一个模型,一个帮助我们理解不同政治行为者之间关系的分析工具。它的两端分别是技术官僚与坚定的儒家士大夫(committed Confucian):前者强调对皇帝的忠诚,依靠专长能力在行政、财政、军事等领域中施展影响;后者则立足于儒家经典与道德理想,主张通过制度设计与教化来约束权力。然而,在现实的政治环境中,绝少有人会完全处于光谱的一端。大多数政治人物在实际操作中都处在这条连续体上的某个位置,随环境与时势而变动(pp. 1-26, 115-142)。
这一模型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打破了“儒家vs.非儒家”这种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也避免了对历史人物的标签化判断。通过“连续统一体”,我们能够理解一个儒家士大夫在某些情境下为何会采取技术官僚式的策略,反之亦然。更关键的是,它让我们看到,在传统儒家史学中被边缘化的群体,也可能在国家治理中扮演关键角色。比如说,宫廷女性、宦官、外戚武官多是通过技术官僚的渠道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传统儒家史学叙事将这些政治势力视作对王朝稳定的严重威胁。蔡涵墨的模型则有助于我们分析这些人物在当时政治光谱上的位置,而非陷入儒家叙事的窠臼。这一方式使得我们能够以更细致、动态的方式理解宋代政权结构的复杂性。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蔡涵墨提出的“技术官僚与儒家制度主义连续统一体”模型,恰好为我在研究生时期所见的那种对立的学术观点提供了一种解释的路径。假设我们同意坚定的儒家士大夫在撰写历史时,确实有其政治意图:他们通过强调自己筛选的先例,试图规范皇权的行使,并将这些理念包装成一套合乎儒家正统的治理蓝图;那么这一部分内容自然在他们所参与编纂的史料中被充分凸显,成为我们今日读史时反复遇到的“理想政治叙事”。
但与此同时,这些士大夫也往往将那些与他们立场不同、行为风格更偏向技术官僚路线的同僚视为威胁。那么他们则会在史料中将此类人物描述为贪污腐化、结党营私、误国误君之徒,进而归咎于这些人导致了国家体制的败坏。这种鲜明的褒贬与价值判断,构成了我们今天在许多宋代史料中可见的一种叙事模式:一方面是对儒家制度理想的推崇,另一方面是对“奸佞”的严厉批判与历史性清算。
蔡涵墨的重要贡献,不在于他选择了哪一边,而在于他让我们意识到,这两种表面看似互相排斥的叙述,其实是出自同一群史料生产者之手。他们既在建构理想,也在排除异端;既在塑造政治规范,也在操控历史记忆。这正是“宏寓”与“连续统一体”两个理论工具的关键所在:它们提醒我们,不应再从价值立场上简单评判孰是孰非,而应深入理解这些叙事如何反映出政治结构、权力分布与话语策略的复杂互动。
当然,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进一步讨论和验证这样一条“连续统一体”。但蔡涵墨的贡献不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终极的答案,而在于他为我们打开了一种思考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本身就是珍贵的:它促使我们跳出既有的叙述框架,去重新审视那些看似熟悉却未被充分理解的史料与现象,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历史复杂性的新路径。在面对史料丰富但解释分歧严重的宋代政治史时,这样一种具有解释力的模型,或许正是我们当下最需要的。






